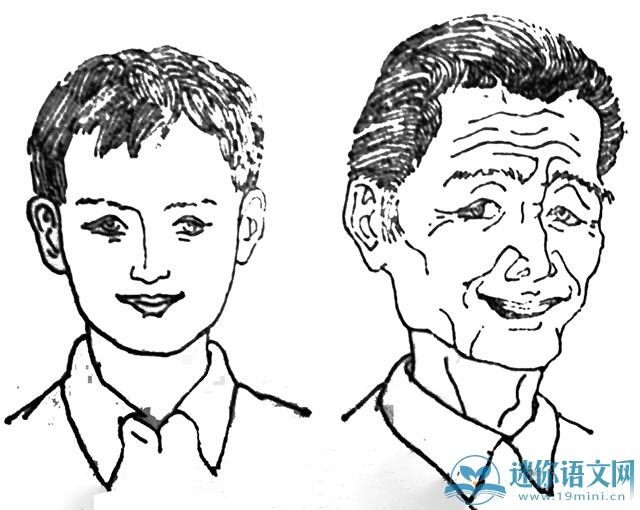写尽世间百态的打油诗
作者/张学民 董晓鸿 日期/2013-02-14 浏览/602
在我国诗歌的海洋中,有一个深受大众喜爱的诗歌流派,叫做打油诗。此类诗歌之所以经久不衰,有极强的生命力,是因为上至饱学之士,下至无知之民均无阅读障碍,都可明了诗中蕴含的思想,并且都还能诌上几句,人人均可“打油”。然而,打油诗自问世以来,却一直未能登上大雅之堂,难望严肃、正统文学之项背。究其原因,大概就是因为打油诗着一个“俗”字。其实,有时“俗”到极至恰恰就是“雅”到极至,大俗便是大雅,用这一标准来评价打油诗应该不算为过。
据说打油诗最早起源于唐朝,是由一个叫张打油的书生开创的一种诗体,他的《雪诗》应为打油诗的滥觞,全诗如下:“江上一笼统,并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。”全诗抓住雪景特点来进行描写,读者仿佛置身于漫天飞舞的雪花之中。前两句由远及近,远处的江面被纷飞的大雪笼罩着,近处只剩下一口水井在人们的视野之中,四周茫茫一片。后两句具体描写近前之物——狗:黄狗已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,白狗身上的积雪使它臃肿了许多。此诗一出,语惊世人,人们纷纷仿效此诗创作方法、艺术风格,给诗坛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打油诗的内容丰富多彩,反映了极其广泛的社会生活;语言大都运用俚俗口语,用明白如话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。
“人家养子爱聪明,我为聪明误一生。但愿生儿愚而鲁,无灾无害到公卿。”(苏东坡《洗儿》)诗中有悖于常情的期待,抒发诗人对朋党相争之祸、摧残人才之行的不平之气和愤懑之情,是对黄钟毁弃、瓦釜雷鸣的社会现实的无声控诉。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,便是乐观旷达如苏东坡,也流露出无奈之情,他在另一首打油诗中写道:“无事只静坐,一日如两日。若活七十岁,犹如百四十。”几多苦涩,几多辛酸,都蕴含在这种荒唐的计算时间、寿命的方式之中,风趣幽默的背后自是含泪的微笑,诗人用打油诗的艺术形式来表达“士不遇”的大主题。
有一被朝廷招安的海寇郑广,因同僚不甚礼遇,于是当众作诗曰:“郑广有诗上众官,文武看来都一般。众官做官却做贼,郑广做贼却做官。”快人快语,直斥道貌岸然的假正经之流,那些不蒙“强盗”之名而所作所为却比“盗贼”更甚的“相群相党,上下为蟊贼”之辈才是真正的强人。这首诗以力透纸背、入木三分的语言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官场的腐朽与黑暗。
打油诗既可言志,也可抒怀。大才子唐伯虎因生活困顿不堪,到了除夕年货还没置办齐全,唐伯虎作诗以咏其事:“柴米油盐酱醋茶,般般都在别人家。岁暮清闲无一事,竹量寺里看梅花。”这种安于贫穷、闲适自乐的情怀,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“安贫乐道”思想的承继,但我们仍能从那个林中漫步的背影中读出落魄、失意的灵魂。张、吴两家为界墙之事争执起来,张家写信求在朝为官的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出面干预。张英得知后,写诗一首寄给家人: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?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张英的豁达大度和明于事理,自然让斤斤计较、鼠目寸光之辈汗颜。于是,张、吴两家各向后退让三尺,才有了后人津津乐道的“六尺巷”,足见这首打油诗的魅力。
有一首极为有趣的打油诗不能不提,这就是明代解缙写的《解嘲诗》:“春雨贵如油,下得满街流。跌倒解学士,笑坏一群牛。”据说是诗人四五岁时,雨天路滑不慎跌倒,惹得周围人大笑,于是“打油”一首,回击众人以解尴尬处境。
在新时期,人们也用这种喜闻乐见的诗歌样式来反映现实生活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,领导干部都下乡深入基层,但所作所为已大不相同,民间的打油诗给作了形象的描绘:五六十年代是“下乡背干粮,干活光脊梁。早上挑满缸,晚睡硬板床”,七八十年代是“下乡坐吉普,小肚吃溜鼓。啥事都不办,一天三块五”。对比鲜明,高下自见。
打油诗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是极为丰富的,而后人必将会发挥、光大这一诗歌传统,使之步入文学大雅之殿堂。